打架是不好的,作者为了鼓励自己,甚至不惜编造了一句“名人名言”:“尼古拉斯•德华•李在他的自传《从精子到公子的巨变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,没有打过架的男人,不算一个真正的男人。”要不是我们的编辑水平高,差点让人信以为真。
与开篇这句不严肃的“名人名言”一样,这是一个县城青年的躁动成长史。

文丨王老虎 插画丨马桶 编辑丨小我
1
80年代的苗乡山落民风彪悍,盛行练武,尤其是一个叫白寮洲的地方,几乎家家户户都会舞枪弄棒耍点功夫。有很多会打拳的师傅农闲时会到县城里来教徒弟,这种师傅在民间称之为把式。
我在上小学之前,体格惊人——惊人的瘦,瘦得像猴子一样。父亲担心我这幅身板日后难成大器,便也请了一个把式做我的师父,教我武术,强身健体。与我一同习武的,还有左邻右舍七八个孩子。
习武,要能吃苦,还要持之以恒。每天天没亮就得起来练基本功,跑步、压腿、站桩,晚上练拳也要到十点以后。压腿的时候,身体靠墙,一腿单立,师父慢慢把另一条腿从下往上拉直到越过头顶脚尖触墙,在这过程中,尖叫声惨绝人寰不绝于耳。
站桩,特别是站坐桩,既苦又枯燥。人半蹲下来,大腿与小腿呈直角,身板与大腿呈直角,这个姿势特别像坐马桶。只是屁股悬空下面并没有马桶,只有一支点燃的香。这一蹲就是一刻钟以上,常常痛得额头冒汗嘴上嗷嗷叫,还得担心香把屁股烫着。
在练武的时候,时常有一帮小孩围在旁边看,特别是我在摆弄刀枪棍棒戟时,他们常常对这些纯手工打造的兵器流露出艳羡的眼神。
有一天,我放在院子枣树下的那根溜圆的齐眉棍忽然不见了,习武之人,兵器简直就是自己的命根。我急得团团转,忽而想起那帮喜欢围观的孩子,于是便跑向后院。果然,三五个小孩拿着我的齐眉棍正在那里哼哼哈嘿。
见我来了,他们仗着人多,也不躲闪,呼啦啦就围了上来。为首的那个叫勇伢子,还挑衅地说来呀来呀来打我呀。或许幼时根本没有敌众我寡的概念,又或许是习武经历给了自己就是功夫小子的心里暗示,我一个扫堂腿就把围上来的第一个人扫在地上,夺过那条渗了我无数汗水的棍子,对着他们就是一顿猛打。孩子们被我这阵势吓坏了,有的哭了起来,有的跑回家不敢出来。
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架,自此树立了我在那一带的孩子王地位。被我打的这一帮都成了我的粉丝,我时常带着他们耍枪练剑,打鸟摸鱼,好不快活。

2
上初中之后,武侠剧和警匪片盛行,校园里也流行成立帮派。靠近城郊菜地的叫菜园帮,住五星村的叫五星帮,住在老街上的叫街头霸王,还有十三个女学生搞了个侠女十三妹,好家伙!有一次,我看见十三妹们聚众抽烟,其中一个脸上还挂着鼻涕,另一个梳着羊角辫穿着花棉袄,简直吓死人。
帮派之间冒点卵事也要约架。约架的形式多样,有时候是群殴,有时候是单挑,有时候则是先谈判而后握手言和。而约架的原因,无非就是“你长太帅了看你不惯”、“你今早干嘛要瞅我一眼”或“你为什么要喜欢小红”之类不值一提的小事。
校外那些二流子社会青年成立的帮派听起来就厉害多了,譬如屠刀会、黑虎门、镰刀帮、锤子兄弟,这些都是真刀真枪的团伙(那时好像还很少提黑社会这个词),打起架来都是乌啦啦的一拥而上。团伙们时常聚集在十字路口,蹲在地上抽烟扯淡,时常一蹲就是几个钟头,也不怕腿麻脚麻。有时候看着敌帮的成员经过,无端端冲上去就开始围殴,我曾亲眼见过一个落单的被十几个人追着砍了几十刀,直到皮开肉绽倒地不起。
我堂哥当年也加入过名头最响实力最强的第一帮派屠刀会,这层关系当时倒也间接地帮了我一点忙。
有一次,班上靠窗的一个同学往外吐口水,正好落到楼下别人身上,楼上这位也不晓得。转眼间,楼下就冲上来黑压压一群人,走到边上就打了吐口水那位一耳光。我正好坐在他旁边,心想怎么着也得劝,于是站起来说算了算了。被吐的那个本来正想对我动手,来者当中不知谁说了句他哥是屠刀会的算了算了。
后来,这事就真的这样算了。

3
高中是所有打架事件的高峰期。
一次放学后在操场上打篮球,空中抢球时我不小心与别班的叫向哈的撞到了一起,两个人都倒地,那小子爬起来后很横,冲过来就推了我一把,众目睽睽前我落不下面子,于是用拳头回复他。旁边一起打球的随即过来劝架,他可能吃了点亏,丢下一句“明天我喊人搞死你!”就被别人拉走了。
怕对方人多,第二天我约上两个同学,都换上了牛仔衣,一人带了把短砍刀,用报纸包住藏到袖管里,在放学路上等向哈。
没想到向哈头天只是虚张声势,根本没喊人来,只是和班上几个同学骑着单车从我们埋伏的路上经过。我们冲上去一把将他扯下来,刀是用不上了,但是暴风骤雨的拳脚也够他受的。我边打边叫嚷:叫你狠叫你狠。他那些同学也不敢动手,倒是向哈自己也算有种,抱着头硬是不吭一声。
人很奇怪,在成年人眼中,初中生、高中生都是小屁孩;可是当你自己所处那个阶段时,却觉得自己很成熟很懂事了。
舞厅其实一般都是大人才去的,但当时我们已经觉得自己是大人了。有一次我和斌哈去舞厅学跳舞,当时流行的舞有一款叫“追鱼”,就是两个人面对面,方向相反但步伐一致,你退我进我退你进,某个节点各自旋转一圈。就这样追着追着就把旁边人的脚踩了。偏偏踩了一伙小混混,也是不由分说,围上来就打。我俩一看对方人多,寡不敌众,趁着灯黑就往出口跑。
那伙人也是吃了饭没事做,又不是深仇大恨,硬是在后面穷追不舍,气得我们边跑边骂娘。跑到十字路口时,有个小个子腿短脚快,把斌哈追上了,照着他头上就是一刀,斌哈面门上立刻见红了。得亏那时正好有警察经过,那伙人才散了。但斌哈额上双眉之间从此却留下了一道竖的疤痕,有点二郎神的意思。
这事的正面效应是,从此斌哈收了野性一心读书,后来考上了北京服装学院,现已成为服装界的一代宗师。
高二时,我喜欢上隔壁班的一个女生,课间休息我时常跑到隔壁去跟她聊天,有时甚至坐到她后面跟别人挤一桌一起上课。有一天下课,我瞧见她班上一个男的正站在窗边跟她说话,而她露出一副极不情愿的表情。我就丢了一句:“别个不想跟你说话你死皮赖脸在这里说什么!”在喜欢的人面前,谁服软谁是孙子,于是我俩很快就扭打起来。
好在拉架的人多,我俩很快就散开了。
本以为这事就过去了,没料到当天放学后,经过那男的家门口(他家就在学校附近),只见他、他弟和他叔三人早已在那候着,冲将过来就是一顿乱打。我倒是不示弱,不管他们怎么打我,只是集中力量攻击其中一个。后来打着打着,我抱着他叔就滚到了路边的刺蓬(荆棘)窝,到处都是尖刺,另外两人也不好跳下来。再后来,来了好多同学,就把这架劝开了。
尽管双拳难敌六腿,我也没吃蛮大的亏,但我咽不下这口气,回家就叫了我屠刀会的堂哥。那时,堂哥在玻璃厂上班,右手正好被玻璃扎伤了,整个手掌打了绷带。他不由分说,左手操了把屠刀,带着我就冲进了对方的家。那三个人听到我们来,立刻从后门跑掉了,只有他父母在家。我们也知道冤有头债有主,除了踢破门,掀翻凳,倒没有做出什么别的出格之事。
这事之后就不了了之。后来有时候看科比右手受伤缠满绷带,改用左手投篮,我总会想起当年那一幕。只可惜科比也成为过去了,不胜唏嘘。

4
大一那年暑假回家,认识了一个开理发店的女孩。女孩长得很漂亮,我头发哪怕稍微长了1.5毫米,就又去找她修。一来二去,她就同意跟我去散步了。
有一天,我俩正在街上走着,忽然有一股天外之力从背后袭来,我一个踉跄差点摔倒。我回来一看,一个敦实的小伙子正怒目圆睁,挥拳扑向我,原来刚才是他施展了一记飞脚。那女孩在旁边大喊:谢逊别打,谢逊别打!
他头上倒时没有金毛,但是力量却有如狮王一般。想必也是练家子,几个回合下来,我竟感觉有些吃力。就在这时,朋友老皮路过,见我正跟人撕打,立刻加入了战斗。他老皮人高马大,我老王手快脚疾,胜负立分,他老谢很快被打得鼻子流血。要不是被女孩拉住,他恐怕受伤更深。
后来我才得知,这个谢逊是女孩家里许的未婚夫,尽管她不喜欢,但人家也是订过婚的。
大二时,我们与楼上的一个女生寝室结成了联谊。她们时常来我们宿舍玩,其中有个醴陵的小女生跟我关系特别亲近,总是叫我哥哥。我也没多想,正好我也没有妹妹。她给我买了几次零食,我带她看了几场电影。
有一天晚上熄灯了,有人在门外喊我出去一下。我稀里糊涂就跟着他来到操场上,那时已经有十多个人等在那里了。其中为首的男生指着我的鼻子问,是不是经常跟那小女生在一起玩,我说是。他又说以后再见我跟她在一起,就会把我打死。这句话一下子把我激怒了,我也不知怎么就冒出一句:要么今晚就打死我,要么明天我拿菜刀一个个砍死你们。
结果,被我这么一喊,再加上那群人也许大部分都是临时叫来站墙子的,大家反而劝我们说算了算了……于是,月色下,微风中,他们跟我一一握手,和平散去。
这不战而胜的场景,让我今天想起都感到好笑。

5
毕业之后,我到深圳工作,与公司里的一个湖南妹子很聊得来。
有天晚上,我俩坐在操场上聊天。来了个保安,问我俩查暂住证,我说你凭什么查证。那保安拿电筒就往妹子脸上照。妹子也是个暴脾气,一脚就踢了过去。保安伸手就打。我一见保安动手了,也起身跟他扭打起来。保安边打边用对讲机喊人,随后就来了七八个人,带着棍子对我就是一阵乱打。妹子在旁边边哭喊边护着我。
那是我吃亏最大的一次打架经历,所幸只是受了一点疼痛,没有一点内伤。或许是之前习武练就的好身板,又或许是老天眷顾我给我好运气。
从这架以后,我逐渐心生静念,虽然不怕死,但也贪生。特别是看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以后,更想好好享受每一天。现在,我常常坐在自己的私人小厨里,炒几个好菜,抿几口小酒,和过来的朋友聊聊彼此的故事。
我不再热血沸腾,只喜欢回忆过去。

王老虎
七十年代生人,籍贯邵阳城步大南山脚下,恬不知耻欺骗无知少女永远25岁。年少曾于省府求学,后入粤求生,辗转澳门,终不得志,返乡长沙,沉迷厨艺,开小饭馆,曰:六扇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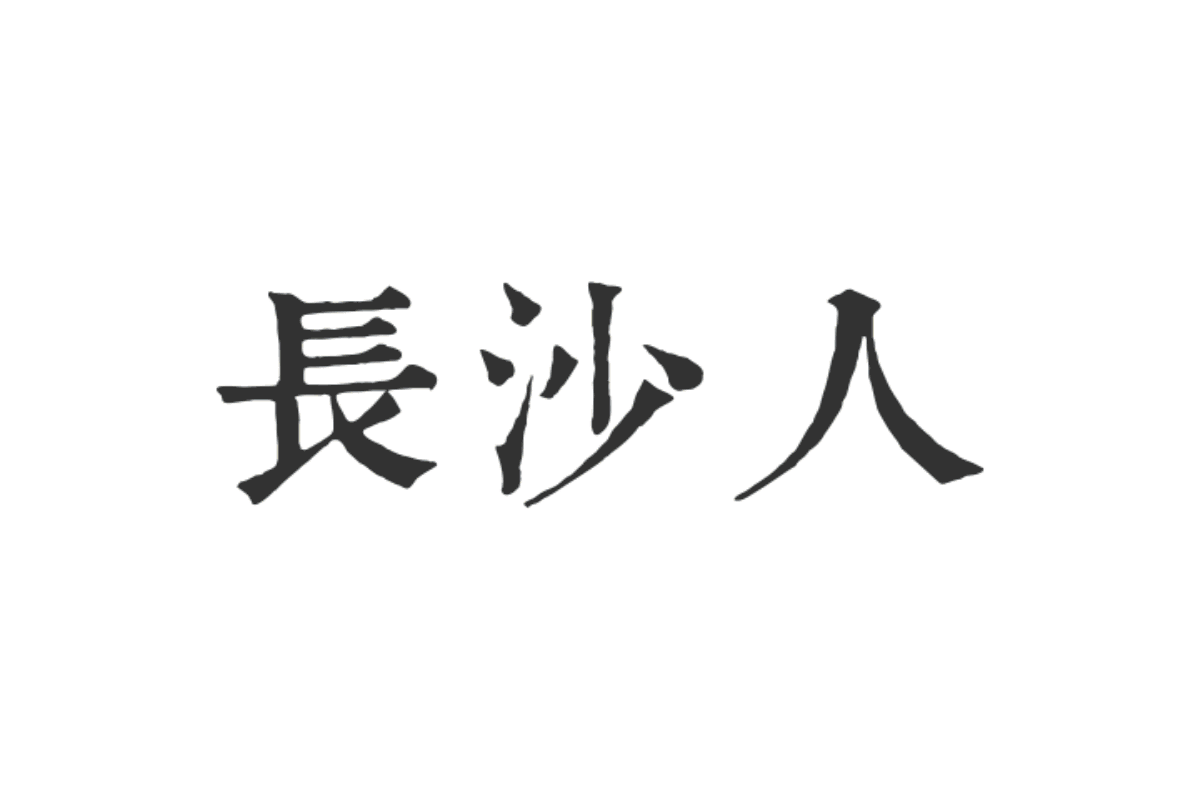
2017-10-10

